赵呆子|妮儿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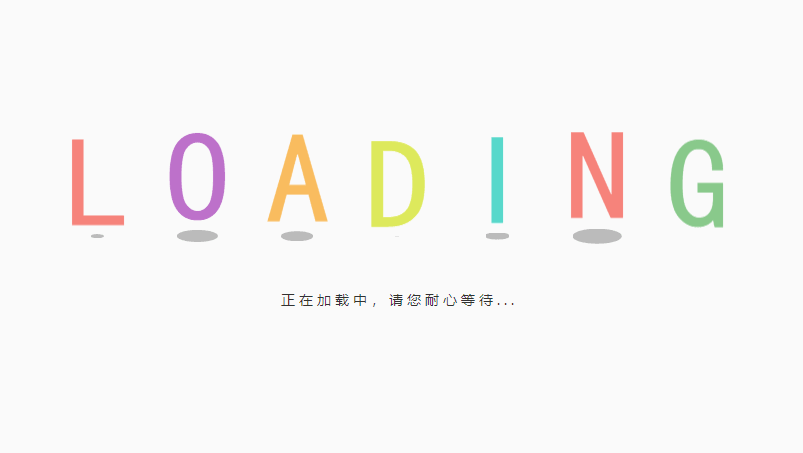
2015年的第一个风雪之夜,妮儿姐耗尽了她体内最后一丝养分,终于合上了被母亲常常说起的那双大眼。
可一直以来,我并不认为妮儿姐的眼大。她看上去个子矮矮的,体态臃肿,体重足有一百公斤靠上,说话大声大气,只是并看不出她的眼大来,笑起来更是,眼睛马上会眯成一条线,显得更小。
可母亲讲起那段往事来,总要强调妮儿姐的那双“大眼”。
妮儿姐,是二舅家的二女儿,1940年生人,我母亲比她大八岁,是她的三姑。母亲常讲的那段往事,大概发生在日本鬼子入侵中原那年代,一天村里人得知要“过鬼子”,便都携家带口往北山上跑,可不知什么原因,外婆一家竟把只有两三岁样子的妮儿姐弃在了家里。
在山中躲避的几天时间里,外婆天天内疚着急却又无可奈何,只不停地求上天保佑她的小孙女平安无事。可母亲说,事实上大家彼时心里都有着最坏的预感,一个尚在吃奶的女娃儿,整整几天几夜,即使躲过了鬼子挨家挨户的扫荡,仅饥饿也早要了她的命,况且那年月还常有进村觅食的野猪饿狼什么的。
可谁想,当鬼子过后,大家回到村子,外婆迫不及待正要家里家外找寻她的小孙女时,一推屋门,便从屋里传来了喊“奶奶”的声音,母亲说,彼时的妮儿姐蹲在屋角暗处的干草堆里,瞪着水灵灵的两个大眼睛,正望着他们笑呢。外婆跑过去一把搂她入怀,哭笑着说,老天爷,俺家的妮儿,命可真大啊。
妮儿姐的命是真大,但不是富贵命,她的一生很是普通,没有大富大贵,也没有大灾大难。在我的印象中,她不象大表姐那样有文化,且自尊自强,上了学,有了工作,且嫁给了一个高大帅的教师,一生过得幸福平安的;她是个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人,也可能因为她太没有什么心眼,二舅担心她未来的生活,在谈婚论嫁时,就招了个上门女婿,让其一生跟在了自己的身边。
打心眼里,我是很羡慕妮儿姐的,依她的性情,我觉得她可能一生都没有认真思考过做一件让别人看上去很有意义的事。从小靠父母,不用操什么心;婚后靠丈夫,且仍在父母身边,还不用操什么心;一生养育了三女一男吧,一个个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她也难免要为他们付出很多,但在外人看来,其付出也全是自然而然的行为,并没有为他们设定什么目标,从而为之努力培养什么的,一切都全交给了时间。至于儿女们都成家了,即使有所不孝,她也没太多的计较,看上去仍乐呵呵的,一幅满知足的样子。这样看似糊糊涂涂平平庸庸的一生,我想倒也再好不过,世上有为天地立命,为民**的英雄豪杰,但更多的是平平淡淡,以自我中心而生活的凡夫俗子,在这凡夫俗子中,能如妮儿姐这样“难得糊涂”,“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不也正是许多先圣贤哲们孜孜以求的理想人生吗?
然而,母亲却不这样认为,特别是在妮儿姐去世的前几天,当母亲看到她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样子时。
那天是农历十月初四,民俗中,农历十月初一是鬼节,要给逝去的亲人们上坟“送寒衣”。今年这几天却一直下雨,等了几天仍不见停,在母亲的催促下,我只好冒雨去给外婆“送寒衣”了。本想母亲年纪大了,又是雨天,行动不便,不让她去了。可她老人家却说很长时间没见“娘家人”了(其实,外婆家和母亲同辈的已经全不在了,只有舅舅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平时偶来看望他们的姑姑、我的母亲,可不知什么原因,今年只见大表姐来过两次),于是只好一块儿驱车前往。
可这一去不当紧,先是见到表嫂不知什么时候得了脑梗,一向说话走路风风火火的她,突然间路走不成了,话说不成了,整个样子都傻呆了许多,但她一看见母亲,便泪流涟涟,也足见她与母亲的感情之深。
接着是去看妮儿姐,没料想比表嫂更不忍视,这回是母亲先老泪纵横!一张并不宽大的床铺上,往昔二百多斤的妮儿姐,如今躺在被子下,如果不是她的头在外面露着,竟看不出被子里盖着一个人!此时,我终于看到了母亲描述的“大眼睛”,皮包骨的瘦小头颅上,只余下那双可怕的“大眼睛”!母亲泣不成声地喊着“妮儿”,妮儿姐也吃力地、用脸上少有的皮肉“堆”出笑来,连连喊了几声“姑”,且如往常一样示意让母亲别急着走,住下来陪她两天。看着一老一少执手面对的情景,我实在不忍再看下去,强忍着泪转身出来,母亲是如何与妮儿姐最后作别的,我不知道。
农历十月十二日下午,天空飘起了雪花,当日夜半,风雪渐紧。第日午饭后,我正围坐在火炉旁听母亲又讲那段往事,妮儿姐的儿子突然打来电话哭道,她妈于昨晚夜半“走”了,并特别嘱我,别让他的姑姥姥、我的母亲知道。
彼时,我一边接电话,一边看着耳背的母亲,心中隐痛着掠过一句话:从此,我年近九旬的老母亲,又少了一个“娘家人”。
【作者简介】赵呆子,原名张国昌,登封人,1970年生,1993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兼及诗歌、小说等。
(责任编辑:副主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