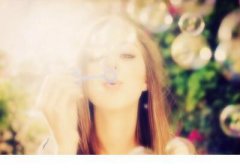百年堡子
|
每次回到堡子,站立在残破凋零、沧桑厚重的百年堡墙下,都会情不自禁地冒出一种无法言表的情愫,好奇、惆怅、伤感、自豪等等。往昔已去,岁月依然,世事烟云,追忆笔下。 堡子位于一个叫陇西川的小山村,始建于1908年。堡墙由黄土夯筑而成,长30米、宽18米、高5米,呈长方形,内部分前后两个院子。堡墙虽经百年风蚀雨淋,除稍墙有些残破外,主墙基本保存完好。 从祖辈的口口相传中得知,祖上耕读于天水。高祖父曾是邓宝珊将军的私塾先生。曾祖父梁锦云是清末光绪年间的秀才,过继给他的四叔,四叔是一名德高望重的风水先生,四处云游讲学看风水,一日行走到老家陇西川,眼看此地风水极佳,便携养子定居于此,开起了商铺,经营粮油盐茶等生活日用品。陇西川当时是方圆三十里的商贸集散地,镇子上建有城池,两河自然形成护城河,城池中心有古乐楼一处,始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历史悠久,人员往来密集,商贸发达。由于生意经营有方,曾祖父积攒了一些银两,便盘下宅基地,张罗乡亲们夯起了堡子,建起了老宅。 堡子从建成的那一天起,就担负起了防卫护家的任务。二十世纪初期,老家一带土匪众多,出入频繁,乡民们时不时被土匪掠抢,有时还会搭上人命。由于堡子易守难攻,据说曾经遭遇过几次小股土匪的攻夺,但都没有得逞。 1920年12月16日发生的海原特大地震,我的老家陇西川一带受灾严重,也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堡子东、北两面的稍墙在这次大地震中被震塌,所幸没有造成院内人员的伤亡。后来,稍墙用土坯子重新进行了修缮。 这座黄土夯起的堡子,虽经百年岁月沧桑,却见证了朝代的更迭,人间的冷暖。堡子里曾经演绎过一场朴实大爱,至今被传为佳话。 1935年10月的一天,中央**(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小村,一名叫曾宪桢的**小战士,年仅15岁,两只腿溃烂,掉队倒在了堡子大门口。清晨干活的长工发现大门口躺着一个人,便通知了我的曾祖母,曾祖母看见小**后,心生怜悯,便收留了他,让他跟长工住在一起,请郎中为其治病疗伤。因腿脚溃烂发臭,一日同屋居住的长工嫌气味难闻,偷偷背着小**扔到了堡子附近的一条水沟里,曾祖母差人找了半天才找到,从此亲自看护照顾,一个月后小**才能下炕走路,认曾祖母为奶奶。后来梁家分给他田地,建起宅子,娶了媳妇。从我记事起,我就喊他大爸。直到去世为止,他一直生活在我老家,视梁家人为亲人。 世代生活在堡内的梁家人,秉持耕读家训,一边辛勤劳作在田地,艰难维持生计;一边省吃俭用,培养读书人。 我的爷爷梁承浩就是从堡子里走出来的读书人。1946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农业技术专科学校园艺专业(现甘肃农业大学前身)。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河西腾格里沙漠边缘一带从事造林固沙研究,1957年出席了全国林业会议,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被尊称为西北林业战线三豪之一(张汉豪、梁承浩、童子豪)。爷爷的一生,可以说是苦难的一生,起起落落,胸怀报国之志,直至1979年才得以平*。 百年堡子,几易其名。新中国建立之初,堡子里面办起了学校,院内的房子当作了校舍,培养出了不少人才。后来,学校迁到了陇西川小学现在的地方,房子被拆盖了新校舍。再后来,堡子又被人民公社征收,先用作饲养场,后又在院内办起了集体食堂。至今外墙体上还保留着当年标语的印记,成了一个时代的留存和见证。 堡子的风水并没有当初祖先修建时想象的那样,走出如雷贯耳的达官贵人,但它遮风挡雨,保护着曾经生活在堡子里每个一人的健康平安,也一直激励着后人勤奋读书,自强自立,逆境奋发。堡子里先后走出了十多位大学生,在不同的城市打拼,开创着新的人生。 时至今日,唯有母亲成了堡子最忠实的守护者。每年清明节一过,母亲便吵嚷着让我们送她回到堡子里,开始大半年的田园生活。母亲会在院子中劈出的几块菜地上,种植蔬菜、花草和果树。每到春天,院内牡丹、芍药竞相开放,蜂绕花香。盛夏时节,辣椒、茄子果实累累,葫芦瓜爬满院子。而我则要经常奔波在老家堡子与城市居所之间,来回200多公里的路程,有时深感力不从心,多次建议母亲不要再去堡子居住,免得儿女操心。但每次母亲态度坚决,说她只有回到堡子,才感觉回到了自己的家,儿女家再好,住着心里也不踏实。面对执拗的母亲,我多次扪心自问,母亲从嫁到梁家那天起,就将堡子视为生命的一部分,与堡子相依相伴半个多世纪,怎能说不去就不去,怎能说割舍就能割舍得下呢…… 百年堡子依然矗立在那里,成了曾经在里面生活过、而今在外漂泊游子情感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