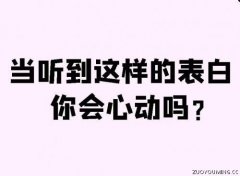麦收最忆是连枷
|
“芒种三日见麦茬。”家乡芒种一到,就开始割麦,忽然想起了连枷。连枷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生产劳动中一种常见的工具,川东北农村的连枷一般是用老鼠刺树条和篾条扎成的。 老鼠刺分布于秦岭以南的山林中,树枝灰白色,枝条匀称,比较平滑,质地柔软。用坚硬树质的树木,先做一个20多厘米长、一头扁一头圆的连枷拐,再用八根老鼠刺树条,两边各四根夹着连枷拐扁的一头,然后分开一字八根排着,用竹篾或构树的皮编织着。再用一根竹竿做连枷竿,连枷就算制成了。 雪亮的镰刀把山上山下的麦田、麦地逐一清理,将那些头头脑脑带走后,麦子就等待着最终的了断。收回的麦子在晒楼上晾干,直到抓过一把麦穗一搓一吹,亮晶晶的麦粒出现在手心时,打麦子的时辰就到了。 看准一个晴天,把成捆的麦子一一解开散在院坝里,人们各执一把连枷,分成两路对面排开,当一边的人一齐将连枷高高举起时,另一边的人一起将连枷砸下。当砸下的一边人举起连枷时,另一边的砸下。那同时砸下的声音,在山间峡谷中回响。 这样反复抽打,一环一环地进行,直到把整个坝子里的麦子都抽打了一遍后,再用洋叉(像长长的弹弓叉,翻麦子的工具)将其翻过来再打。周而复始,反复多遍,让麦粒与麦秆、麦糠慢慢脱离,再经风车或簸箕劳作,麦粒与麦糠就完全分开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年年都要种大片大片的麦子、荞麦、豆子,一年内会在几个时间段里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连枷。 每到打麦子时,父母会带着父亲制作的轻便而好使的连枷,到各家去打麦子。那一班人有十个、八个,四个或者五个分成一组,两队相向站成两排,步调一致地手握连枷,扬起而打下。连枷声声响,粮食粒粒下,慢慢从打场的这头碾向那头,有韵有致,恰似打场里的一道风景。 每次打场要五六天才结束,劳动报酬是记工分,年终分口粮。每到生产队打麦时,我就好像是他们的尾巴,跟在后面一路小跑来到打场,在场上麦垛旁和一群小伙伴捉迷藏。身上被麦芒扎起红红的点子时,仍不顾大人的责罚,还大汗淋漓地一个劲傻玩,玩累后就躲在麦草里睡觉。直到麦子打完分粮回家时,我们一群玩伴才依依不舍地散伙。 后来,村里用上了机器,脱粒机把连枷淘汰出局。记得村里先是很稀奇地出现了脚踏打谷机,用脚踏打谷机打麦子或谷子,虽然省了时间,但力气并不少花,半天下来,脚又疼又麻。之后又有了电动打谷机,省时又省力,彻底取代了连枷。 没有了连枷,而“连枷”一词也几乎被人们忘记了。也许我们无从考证连枷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中写道:“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在宋代时,连枷就已在农村生产生活中得以广泛应用了。 宋代的连枷声声,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从人们的心灵深处传来,并且夹杂着人们劳作时汗流浃背的身影,抑扬顿挫地响个不停。现在,连枷走出人们的视线,或许将被后人所遗忘。 前几日路过旺苍县大德镇,在街上发现了连枷。那几把连枷与电动脱粒机摆放在同一位置,让我感受到庄稼人和连枷结下的难以割舍的情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