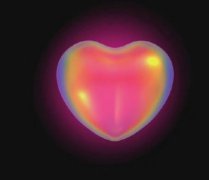父亲和我
|
那年我九岁,父亲四十七。 父亲非常严厉,尤其是对我们三兄妹,而我还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九岁的我开始试着顶嘴,试着我行我素。记忆中深秋的一天下午放学后,父亲问我,在学校表现得咋样啊,我伸出大拇指在他面前晃了晃说:“第一。”父亲暗喜,笑呵呵地问我啥考得第一啊?我说:“拔骨碌、打仗排第一。”父亲的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抡起巴掌狠狠地抽了我一耳光。我被打懵了,我瞪着他,两个拳头攥得紧紧的,心里满满的不服气。年幼无知的我,长大之后才懂得,父亲这是恨铁不成钢。 那年我十岁,父亲四十八。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没有正儿八经休息过,总是从早忙到晚。即使在三伏天,他也会像往常那样忙里忙外。哪怕是碰到下雨天或是下雪天,也不会停下来。 “一辈子就知道上班干活,家里的事一点也不管。”母亲经常这样抱怨父亲,脸上却挂着微笑。“一家老小就是靠国家给的工资生活,不努力工作能行么?”父亲经常教育我们,拿着国家的钱,就得好好干工作。在淄博陶土矿工作的他,有一次带队下煤井检查安全工作,一不小心被钢丝绳绞去了三个脚趾,鲜血哗哗直流,疼得父亲竟然咬破了嘴唇。被人送到医院时,父亲已经昏迷。躺在病床上的父亲,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夫,我还能上班吗?”父亲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会管理、聚人气、有担当,每年都能超额完成任务,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 每逢周末或者寒暑假,我都会跟着父亲去单位。他工作时,我就一个人在旁边玩。记忆中的大企业就是我这个村里娃的天堂。留给我印象更深的是父亲开会时,会场经常出现争吵,年少的我不懂为何总是吵架。父亲的同事周叔叔告诉我,“争吵都是为了工作。只要为了工作,相互批评几句都是应该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现在看来,这也许就是那时企业的民主生活会吧。 那年我十四,父亲五十二。 “公是公,私是私,人要干干净净做事。”父亲的话永远深深印在我的心底,这是我接受的最早的廉政教育。父亲是生产副矿长,那几年正是国家煤、水泥紧缺的时候,只要手上一签字,货就能发出去。当年父亲喜欢抽烟,嗜烟如命,有很多人为了达到目的就给父亲送香烟找父亲批条子。但是每次父亲都会在与客人的撕撕扯扯中拒绝。不久之后,我发现经常烟不离手的父亲,竟然不抽烟了。原来,为了不给送烟的人留机会,父亲毅然决然地把烟戒掉了,从那以后我再没见父亲抽一支烟。每当夜深人静,回忆儿时旧事,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父亲的一举一动影响了我的一生。 那年我十六,父亲五十四。 我们一天天长大了,父亲也老了,不知不觉已到了内退的年龄了。姐比我学习好,又是个女孩,父亲考虑让她接班。对此我特别不理解,晚上也睡不着,反反复复地考虑,父亲为什么不让自己接班。一天早晨,父亲起来做了一道我过年才能吃上的菜,芹菜炒肉,另加两个白面大馒头,我流口水了。父亲说,儿啊,快快吃吧,爹对不住你啊,你是男孩,别跟姐争了,你脑子活,以后一定会有好工作的,我含着泪吃完了我最喜欢的芹菜炒肉。从此我开始发奋学习。 少时一家五口,仅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生活,家庭经济拮据。母亲在菜园里种了些西红柿、黄瓜等蔬菜,变卖后补贴家用。每到周末,天不亮,父亲就把我叫起来,爷俩交替着推着装满蔬菜的手推车,步行几十里,从博山翻山越岭推到莱芜境内,卖完后,再步行几十里回家。一路上,父亲都会给我讲,“孩啊,土地养人,但是只能养活人。要想出人头地,还得好好读书,走出这片山。”我知道,这来回几十里路,是父亲给予我的特殊家教。眼前,是佝偻着腰推车的父亲,背后是贫瘠荒芜的山地。我下定决心,一定走出这片山,要给父母创造更好的生活。 今年我四十九,父亲八十七。 我做到了,走出了那片山,成为一名检察官。记得接父母进城时,母亲嘀嘀咕咕舍不得村里的老屋,而父亲则是一脸幸福的微笑。多么熟悉的笑容!就是这个男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总是微笑着扛起着一切,却给了我整个世界。如今我也成了一个22岁孩子的父亲,我更懂得经营父亲的爱,体会到了父亲的艰辛。家庭的责任,工作的压力,让我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再忙再累,我都按时去父亲家里陪他聊天。当年他失去的三个脚趾处,时常会发炎、痛痒,我尽量抽出时间去父亲家中帮他掐掐揉揉。 时光太无情,原本强壮结实的父亲,如今被岁月摧残得瘦骨嶙峋,原本笔挺的腰杆也早已弯曲,满头的黑发已变成银丝。唯一不变的是那份无私而深沉的父爱和对儿女永远的牵挂。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匆匆往事如云烟。很久以来,就打算抒发一些发自肺腑的话,在心底酝酿了很长时间。但是,却发现,一些话,就这么几句,却仿佛永远也说不完;一些情,就那么简单,却如桑麻般越织越密。或许父爱如清茶,只需品尝,不需言语,便已经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