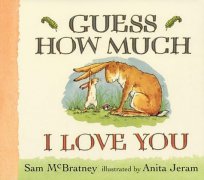崖前的那棵核桃树
|
崖前的那棵核桃树 郝跃红 一个常与树对话的灵魂,注定是孤独的,但也是纯粹的。当我最后面对丢在院子里曾是树的躯体现在却已成干柴的那一段木头时,精神的家园里有一种“呼啦啦”大厦倾的覆灭,噢,崖前的那棵核桃树。 菜园的树都英年早逝,一锹刨下去,根扎在发红的粘土里少了根须。这种粘土在北方可以和着煤面烧火,自然是养不活一棵树的,更不可能让它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了。但崖边的那棵核桃树却奇迹般地活了很多年,并伸展着它的枝叶,昭示着它的青春。 树大,叶大,树荫自然也大。盛夏,拿个小凳子坐在树下读书,很是惬意。有时累了,我就靠着树干休息一下,是那么踏实,像是依在了爷爷的怀里。秋天,特别是深秋,风一吹,叶子嘁嘁喳喳一阵私语,就带着它的果实一起从树上落下来,“嗵”的一声,伴着很大的声响。我常常会欣喜地跑去捡起带着绿色外壳的核桃,有时外壳会摔碎,露出里面的核桃来,再扒掉薄薄的那层膜,就吃到鲜美的仁儿了。但许多时候是等不到深秋的,我便踩一个高凳,抓住细一些的枝条,一个翻身跃上去,找一个长棍子,“噼噼啪啪”一阵乱打,枝、叶、果实都会统统被敲下来。那时的壳儿紧紧地包裹着核桃,如母体中的婴儿,想剥离是不容易的,要放好长一段时间,等外壳渐成纤维状,才可以剥落。有时就直接放在砖头上硬砸,硬抠那一点仁儿,两手就会被染成黄绿色,隔夜就会变成黑色,久久地洗不掉。 爷爷最喜欢在停电的晚上给我们讲故事,让我们猜谜语。他说:“盆盆扣盆盆,里面盘着两条龙,是什么?”我们会很快地回答:“核桃!”再次吃到核桃时,我就特别注意它那外壳,疑惑上面的皱纹怎么会爬到爷爷的脸上。再扒里面的仁儿时就特别怕碎,怕失去龙的形状。有时爷爷会拿着几个核桃扔来扔去,看着上下翻飞的核桃就想起魔术表演来。后来渐渐地,我们也可以拿着两个核桃扔着玩儿了,但只是两个,爷爷可以玩儿到五个。有时,爷爷也会把手背在身后让我们猜,猜中核桃的就有的吃,猜中空拳头的就是一个脑瓜嘣。爷爷告诉我们说:“吃核桃会补脑,想聪明要多吃!”我问:“为什么呀?”爷爷说:“吃什么,补什么,你看看核桃像什么。”我终于明白。渐渐地,我发现我们家的核桃个儿小,壳儿溜圆,大概是木质的缘故。怪不得爷爷常说红儿的脑袋比咱家的核桃还难开窍。 中考的成绩远远地超过了重点线,父亲却不让去,我便辍学在家闹,流着泪水站在菜园里摇撼那棵核桃树,却摇撼不了父亲的决定。九月的核桃还嫩得毛茸茸的,我在树上乱打,那么得狠,用小刀在树上乱刻。我讥笑它,看看你的叶子,没有枫的形状美,没有枫的色彩艳;看看你开的花,毛茸茸的像一条绿蜈蚣;看看你的树干,粗糙,干燥,除了能烧柴别无大用。人们赞扬春风中的柳,夏日中的槐,秋天里的枫,寒冬中的松,你伫立在这崖边,显得多么丑陋。之后很多年,我很少再去关注它,轻浮的年轻作出了轻率的决定:我不再好学! 我再次注意到核桃树时,是一次归家的时候。远远地就望见了立在崖边的树,好像它一直在召唤着我回家,但这一次我却发现它突然变得瘦了,小了,纤弱的枝条上写着:枯败!只在树的顶端举着那么一点点绿。尽管这样,在深秋,还是结出了几个小小的核桃。我突然觉得它老了,禁不得风霜了,干瘪着,只有苟延残喘的力气了。那时的爷爷已经中风躺在床上几个年头了,我坐在他的床前,他的嘴一张一翕地说不出完整的话来,只有混浊的泪水在眼角蠕动着,“籁籁”地流了下来。我跑到菜园里,站在核桃树下抚摩着它干裂的枝干,默默地流泪,想它是那么坚强,那么执拗地站在这里,看着红颜薄命的杏、梨努力地把根扎下去,扎下去,把叶伸展开,伸展开,挺立成崖边的一道风景。生命,原来是一种坚韧,也是一个过程。现在它老了,终于是老了,而我却无奈到了顺从。 爷爷走的时候还有初春的料峭。核桃树秃噜着几根枝杈,伸向灰色的天空,显得那么怪异而苍凉。它看着脚边的小草破土而出,那点绿像是把它带回到了许多年前,它曾是那么欢欣地生长着,也曾在夏日的狂风中举着枝条跳舞,也曾在秋日的晚霞中投下了斑驳的身影,一年一岁,一枯一荣。但现在,它终于是吐不出那一点点绿了,它已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连一声叹息都没留下,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走了。 那棵核桃树,立在崖边,终于,走完了它艰难而又卓绝的一生! (作者单位:山西寿阳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