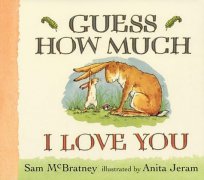我是吃过亏的
|
我是吃过亏的
十多年前我收到过一份小朋友们编的报纸,名称记不得了。我很高兴,因为我自己念初中的时候也曾在两张日报上编过两个周刊。那是在青岛市立中学,同黄宗江一起。那时候我十五岁,黄宗江十三岁,现在他是影剧界和文艺界的一位大名人。我高兴的同时还起过投稿的念头,不知怎的没有写。后来那份报纸不再寄给我了,没法联系,至今引以为憾。 我想写的是建议读者看重背诵,最好从小开始背诵一些东西,因为我在这方面是吃过大亏的。一则,小时候背熟了的一辈子记得住;二则,更重要的是,记忆力是需要培养,需要锻炼的,背诵是最现成的好办法。过目不忘的人确实有,那种人得天独厚,但是为数不多。 鲁迅先生说:“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加些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我写文章也想这样,但是那种笑谈或闲话之类往往记不确切,下笔的时候用不上。这是举例而言。多数场合并不是那种准备作为夹杂之用的闲话或笑谈,而是打算据以为文的很重要的内容,动笔的时候记不准确也找不着了,想写的那篇文章就只好放弃。这才痛感记得住读过、听过或经历过的事多么重要,特别是记得住读过的东西多么宝贵。每逢这种时候,懊恼之情可想而知,但是已经追悔莫及了。 我不是个很笨的人。拿记忆力来说,本来也不算太坏,问题在于我不仅没有有意识地加以培养,反而以不记忆为荣,以记不得自喜。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人吗?我写过一篇小文章──《我要埋怨三个人》,其中的一位,是我初小时期的柳老师。请他在天之灵宽恕我,宽恕我把责任推给他。因为不抬出他老人家来,这件事说不清。这位柳老师很严厉,背不出书的要打手心,是真打,不是做做样子吓人的。他的儿子也在我们班上,他打得特别凶,但是他惟独不打我。同学们当然不平,有一天便鼓噪起来:“李某某也背不出,老师为什么不打他?”正当我惶惶然不知所措的时候,柳老师一脸正气,凛然说道:“背书是为了作文,李某某作文好,我为什么要打他,你们要向他学。” 请读者诸君想想看,当时我多么高兴啊!后来我才知道伯乐识得出千里马这个典故,其实那时与其说是柳老师发现了我这匹千里马,不如说是我发现了我自己,一是发现自己作文好,二是发现我背不得书不仅没有什么不好,而且背不得有理,背不得光荣之至。 我今年吃八十四岁的饭,回想这几十年来,在通常情况下,我可以说没有一天离开过书本,但是阅读很不认真。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翻得倒是挺快,几乎像个才子,不过书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却只有隐隐约约的印象。别人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我是读的时候根本没有装进去。顺便说一句,最近这十多二十年来,我很勤奋,很用功。要是从小就这样,我这个人也许会很了不起的。现在我补课认真阅读,间或练习背诵格律诗,还是有点好处。可以说我现在每天都能享受学到一些新知的快乐,记忆力似乎也有所长进。所以我很高兴地说:只要想进步,永远不太迟。 有一次我同我的一位亦师亦友的老朋友黎澍谈天,他是大历史学家、思想家,文章也写得很漂亮。我说起我这段经历,他说,那可真糟,他的老师却很看重背诵,叫他们背《水浒传》;说着说着他就背起来,真正如俗话所说,滚瓜烂熟。我大吃一惊,没听说长篇小说也是可以背诵的。难怪他中学时期的同学都佩服他记忆力好,他喜欢辩论,引经据典,张口就来,不用查书。他同钱钟书是好朋友,两位大学者探讨学问,旁征博引,也都如探囊取物。钱钟书对人说过,他年轻的时候确实过目不忘,我想那真是天赋。至于黎澍,禀赋固然不错,小时候背诵《水浒传》之类的锻炼,对于加强他的记忆力,想必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旧时代的所谓读书人,必须背四书、背古文。直到20世纪初年新式学校兴起以前,青少年只有那一门课,没有史地、数理化之类。那时候有些人学古文的方法,是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贴在墙上,背熟了之后天天揣摩钻研。那些文章一般都不长,每篇不过千把两三千字。这样精心背诵揣摩的文章,我猜想一辈子大概也不可能很多。 现在背什么好?我建议背《千家诗》,现在有新编的版本,最好从三四岁开始。去年老友侯祥麟院士九十初度,寿宴上他那个三岁多的外孙女背了好几首唐诗,背完一首自己先鼓掌。什么“故人西辞黄鹤楼”,什么“朝辞白帝彩云间”,她当然一点也不懂,这没关系。我的意思还是那两句话:将来懂了用处很大,更重要的是培养了记忆力。格律诗讲究平仄,又必须押韵,因此极便吟唱。孩子们背起来琅琅上口,像唱儿歌一样。那天我跟着她背,跟着她鼓掌,玩得十分痛快;同时得到了很大的启发,随后就买了好几本《千家诗》,分送给亲戚家的小孩子。 这本《我们怎样学语文》,我想用意是希望有助于青少年提高语文的阅读和写作水平,这点我十分赞成。写到这里,再说两句:首先是多读课外书。正规的学校教育很要紧,从小学起到大学,目的是学习做一个真正的人,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这方面我不多说。我这里只说学知识,我认为学校主要是教授一种方法,指点门径。这意思是说,课堂上老师讲解的内容很有限,等于一小匙一小匙地喂,虽然必不可少,但是分量很不够。所以,人们要想成大器,必须多读课外书。拿我自己来说,很惭愧,我这一辈子除了耍耍笔杆,百无一能。而且所以还能做做这件事,全靠课外看书。虽然从小学到中学,所有的“国文”老师都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们,但是我从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恐怕不很多。我深深感谢的,是他们鼓舞了我的信心。就说那位柳老师吧,我埋怨他,同时也感谢他,感谢的成分也许更多一些。 其次,讲到写作,目的不是希望人人都成作家,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写封信、写篇论文,准确和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却是人人都应当做到,也是能够做到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人文化水平的综合表现。我曾说过一句笑话,比如打乒乓球,不可能人人都成庄则栋,但是,打到一定的水平,是人人都可能的。这是许多年以前的话了,那时候打乒乓球庄则栋最有名。可惜现在有些学士、硕士,一封信也写不通顺,或者写个请假条也免不了错别字连篇,这样的笑话就太不应该了。 附记 这篇文章写完以后我才知道,大历史学家钱穆背得《三国演义》,这是背得出长篇小说的又一例,看来他全本都能背,随便你指哪一段,这对于我又是一条大新闻。我是刚刚从林谷《说钱穆》一文中读到的。作者从钱穆的书《八十忆双亲》引用了一段,照抄如下: 一客忽言:“闻汝能背诵三国演义,信否?”余点首。又一客言:“今夕可一试否?”余又点首。又一客言:“当由我命题。”因令背诵兼表演,为诸葛亮,立一处;为张昭诸人,另立他处。背诵既毕,诸客竟向先父赞余,先父唯唯不答一辞。翌日之夕,杨四宝又挈余去,先父亦不禁。路过一桥,先父问:“识桥字否?”余点头曰:“识。”问:“桥字何旁?”答曰:“木字旁。”问:“以木字易马字为旁,识否?”余答曰:“识,乃骄字。”先父又问:“骄字何义,知否?”余又点首曰:“知。”先父因挽余臂,轻声问曰:“汝昨夜有近此骄字否?”余闻言如震雷,俯首默不语。 引文的后半段显出一个好父亲的形象,他深谙教子之道。林谷紧接着发了一通议论,称赞“这真是一种绝佳的启发式教育”,说得对。我在此向这位好父亲的在天之灵表示敬佩之意。虽然我不完全赞成他的见解,但是他的方法是好的。我这意思是,骄傲不好,骄傲可能使人固步自封,但是小孩子的骄傲中往往包含着自信,这自信却是很珍贵、值得鼓励的。所以我认为,对小孩子的骄傲,我们大人不要警惕性太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