碌碌:户口簿上的过客
|
但是,除了同村的人之外,每个见过我父亲的人,都不相信我的这一段描述。行走在贯穿村子的河塘边,如果你看到一个老人拿着拖把,在河水中搅动,然后拧干,端着拖把慢慢往回走,衣衫陈旧,满是尘土,仿佛几个月没有洗过,没错,那就是他,我的父亲。 我很难用一个或者几个词来概括我的父亲,因为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 比如,他是一个不会种地的农民。父亲出身穷苦,家中经常揭不开锅,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找不出来。父亲兄弟姐妹5人,他排行老二,几兄弟中唯有他一人学业优秀,因而全心读书,反倒不会种地。1960年,20岁的他考入当时的南京工学院动力工程系,由此离开农村,成了“国家户口”。5年后,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大连的一家炼油厂工作,从此在那里度过了将近20年“单身”生活。 人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过这话似乎并不适合父亲。即使到现在,他的衣服总也洗不干净,领口袖口总是发黑。他的手总是黢黑,如果没有人提醒,好像他也总是会忘记洗手。他头发蓬松,即使有人提醒,他也不会认真拾掇干净。无论什么衣服穿在他的身上,总是给人不端正的感觉,仿佛那衣服根本就是别人的。这一切都给他贴上了永久的“农民”标签。 在大连的20年可能是父亲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在那里入了党,成了这个国营大厂的技术骨干。1976年开始,他作为中国专家组的成员,参加援建朝鲜枇岘炼油厂,先后三次去朝鲜工作,负责设备安装和人员培训,并因此获颁勋章,受到**和金日成的接见。我们从散落在家中的旧照片里看到了当年父亲风华正茂的身影——整齐的三七开发型,笔挺的中山装,灿烂而不失端庄的笑容,巨大的花环套在他略显瘦弱的身躯上,虽有些滑稽,却难掩意气风发。 这正是我和弟弟先后降生的时间。父亲和母亲1965年经人介绍相识,3年后结婚,几乎从一开始就常年两地分居,每年只有短暂的探亲时间可以相聚。母亲在30岁那年生下我,信到父亲手中的时候,已经是7天之后。再过2年,母亲在南京出差途中生下弟弟,父亲又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直到我12岁之前,我们每年只能和父亲见面一次,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头脑中几乎没有“父亲”这个概念,更不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直到6岁前后,我才突然意识到,父亲可能是个“城里人”。因为我发现,在村子里,别的孩子都是叫父亲“爹爹”,只有我们兄弟俩被要求叫“爸爸”。 那时候我很愿意叫“爸爸”。他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每次从遥远的大连回来,总要给我带一些漂亮的书和本子,其中包括在农村小学永远也用不上的英语本。仅有的一次,他还带我去了上海,住在外白渡桥附近的上海大厦,在豫园的某家书店给我买了全套《三国演义》连环画。 我有好几次在梦里再见那套《三国演义》。这书给我的印象至为深刻,以至于我的儿子一到能够读书认字的那个年纪,我就迫不及待地也给他买了一套同样的《三国演义》。我没有办法让儿子像我当年一样珍爱这书。每次走进儿子的房间,看到架子上蒙尘的这套书,我总是要提醒他把书收好,千万别少了一本,哪怕是卷了书角也不行,仿佛这就是当年我自己手边的那一套。 7岁那年,我离开农村,转学去了邻县县城的一所很好的小学。因为年龄比较小,又从农村来,不得不又参加了入学考试。我至今也还记得老师嘲笑我不会说普通话,把“春天”读成了qun天,这农村孩子不能幸免的毛病让我自卑了很久。有一天,我的音乐老师看到了父亲从大连给我买的一本音乐课本,从我手中“借走”。从那以后,那课本成了音乐老师手中的教科书,再也没有归还。我还记得,我们跟在老师后面,照着那本书学唱“生产队里来了一群小鸭子”。我的心里美滋滋的,看,这书是我爸爸买的,你们城里孩子也没有。同样的事情后来也发生在了数学老师身上。有一天她发现我有一套数学计算练习卡片,也毫不客气地“借走”了。有一次,老师把这卡片印成卷子发给大家考试,我很不幸地做错了2道,收到卷子的那一刻,我在心里发狠:“早知道不把那书借给老师了。” 直到初中阶段,我才更深刻地意识到父亲身份的特殊性。在那个“城市户口”、“农村户口”泾渭分明的年代,父亲的“城市户口”是最大的资产,我们全家都跟着沾光,可以到粮站领到口粮,我们从小就不用种地。看着身边的亲友们为了转户口绞尽脑汁,自豪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今天的人可能无法理解的是,从朝鲜回国之后,已经成为所谓“中层干部”的父亲并没有想办法把我们全家转往大连,而母亲对于脱离农村也并没有想象中的积极性。结果是,1985年,受尽两地分居之苦的父母终于决定,父亲放弃在大连的一切,调回家乡的小县城,在一家县属企业从事技术工作。直到2000年退休,父亲处在一种按部就班的工作状态,没有惊喜,也没有激动。他常常被安排去做很辛苦的工作,他的公司因为他的存在评到了很高的资质,接到了重要的订单,而他自己却所得甚微。他虽有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和总工程师的头衔,退休工资却也不过六七百块。这种碌碌无为的工作经历,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无法理解。 一家人团聚之后,父亲的“神秘感”逐渐消失。长期的分居使得他和这个家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隔膜。在很长时间里,在大家的眼中,他仿佛是一个外星人,他的一举一动都和大家格格不入。他的动作总是很慢,走路如此,做事如此;他的语言奇特,总是时不时地蹦出几个北方话,他喊年轻人为“小伙儿”,至今还被亲戚们嘲笑;他吃饭的时候总是努力地包住食物,避免发出咀嚼的声音,这种很慢的“吃相”也成为笑柄。长期的单身生活让父亲对于家庭生活很难适应,常常不知所措。除了上班,他无所事事,与家人对坐,他也是一言不发,如果没有人安排和指挥,他连打扫卫生也不会想到。 工作和生活中的“平庸”,使得父亲不可避免地成为母亲数落的对象。在每个亲戚的眼里,父亲就是“逆来顺受”的代名词。多么激烈的言辞加诸其身,也不会激起他的反抗;多么痛苦的事情降临,也不会让他崩溃。他的忠厚老实和沉默寡言远近闻名,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怀疑他根本就失去了说话的功能。无论大事小情,没有人会征求他的意见,他也坦然接受别人做出的每个决定,接受每个决定产生的后果。在几乎每个熟悉他的人眼里,他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也是一个对别人没有要求的人。 但我知道这并不是事实。我还记得,上中学的时候,父亲时不时会走到我身边,问上几句学习情况,嘱咐几句上课要认真、考试要仔细云云。不幸的是,那都是我正在做作业、心神最烦的时候,他的话总是左耳进,右耳出。我那时常和弟弟有矛盾,父亲却总是怪我,说什么“大的要让小的”,我照例把他的话当“耳旁风”。现在轮到我自己了,一年前,儿子也开始抱怨我太啰嗦,对我的话不但不听,而且出言相讥,但我依然忍不住要“啰嗦”,仿佛不这样就是不负责。我突然明白了父亲当年的心思。
他的头发依旧浓黑,既能大块吃肉,又能粗茶淡饭,随遇而安,碰到有人问他要不要喝酒,他也会不好意思地说声“好”。他从不早起晨练,也不饭后百步走,他只是扫地、挑粪、拖地,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让他去哪里就去哪里。但他却会在深夜爬起来看意甲,遇到国足的比赛更是不肯放弃,他总是默默地看,不高兴也不沮丧,不评判任何一名球员,以至于我一度怀疑他是不是真能看明白。 我不确定他有没有特别惦记的人,一年到头,我们都不会接到他主动打来的电话,也从不会听他说起某人。2010年是他大学入学50周年,我们问他是否想看看当年的同学们,问了许久,也没有得到回答。 看起来,他并没有什么很执著的追求。有很长时间,我们兄弟都没有回过父亲的老家,去祖坟上烧几张纸钱。逢年过节,父亲总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回去一趟,也很少会喊上我们兄弟随行。几年前,我们终于带着孩子一起回了趟老家,爷爷奶奶的坟头其实早已被夷平,湮没在不知哪块农田中,父亲和叔叔只是凭着印象找个“大约摸”的地方,领着我们磕几个头,烧几叠纸了事。 就在这一次,在城市生活的我们突然发现父亲的祖屋视野开阔,绿水环绕,更重要的是,远离工厂和公路,保持着宝贵的“原生态”。我们提出也许可以把祖屋翻修重建一下,以便将来回乡养老。 这想法却勾起了母亲的不满。她提起,十多年前,父亲已经“自作主张”放弃了祖屋的分配权,全部让给他的两个兄弟了。她埋怨父亲说:“我当时就说过,你自己不要,儿子们如果要怎么办?现在好了,你不相信吧。” 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时刻。无论母亲怎么说,父亲始终一声不吭。好在我们只是突发奇想,并不当真。在我印象中,这是父亲少有的毅然决然的事迹,并且不容商议。那间不大的祖屋住着三叔、四叔两家人,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在我看来,父亲更像一个“过客”,来过,活过,辉煌过,平淡过,甚至憋屈过。这个老牌大学生是一个聪明人,当他选择离开城市回到家乡的时候,可能已经想好了未来的生活,选择了就不再后悔。每个人都在念仓央嘉措的诗“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但似乎父亲是那一个悟透的人。 (作者系南方周末记者) (责任编辑:副主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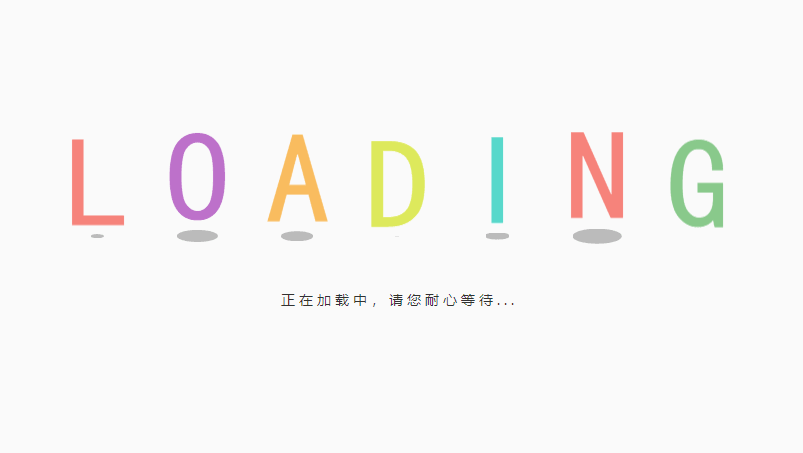 在我们兄弟离家远行之后,老家只剩下父母两人。已过古稀之年的父亲已经身形佝偻,皮肤粗糙,脚步滞重。除了听见孙子叫一声“爷爷”,或者打麻将和了牌,他的脸上会绽放灿烂的笑容,多数时间里,他都是眉头紧锁,仿佛心中千头万绪,愁肠千千结。其实我知道,这标志性的面部表情只是因为遗传,我和我儿子的脸足以说明一切。
在我们兄弟离家远行之后,老家只剩下父母两人。已过古稀之年的父亲已经身形佝偻,皮肤粗糙,脚步滞重。除了听见孙子叫一声“爷爷”,或者打麻将和了牌,他的脸上会绽放灿烂的笑容,多数时间里,他都是眉头紧锁,仿佛心中千头万绪,愁肠千千结。其实我知道,这标志性的面部表情只是因为遗传,我和我儿子的脸足以说明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