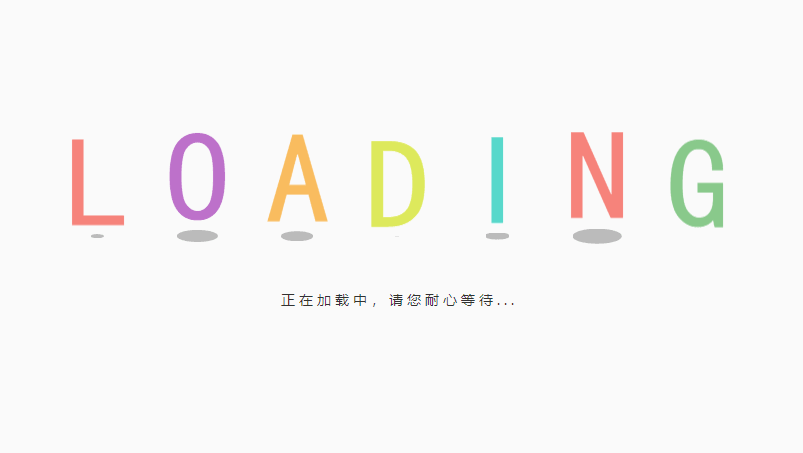亲爱的父亲,我为什么怕你
|
最亲爱的父亲: 你最近曾问我,我为什么说怕你。我试图以笔代言来回答这个问题,即便如此,所写的也仅仅是一鳞半爪。因为就在写信时,对你的畏惧及后果也阻塞着我的笔头,而且材料之浩繁已远远超出了我的记忆力和理解力。 假如你是我的朋友、上司、叔伯、祖父甚至岳父,我会感到很幸运。唯独作为父亲,你对我来说太强大了,特别是因为我的弟弟们幼年夭折,妹妹们都比我小很多,这样,我就不得不独自承受你的头一番重击,而我又太弱,实在承受不了。 比较一下我俩吧:我,简言之,耽于梦幻、喜欢孤独。你则强壮、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说会道、自鸣得意、高人一等、坚韧沉着……总之,我俩截然不同,这种迥异使我们彼此构成威胁。如果设想一下,我这个缓慢成长的孩子与你这个成熟的男人将如何相处,就会以为你会一脚把我踩扁,踩得我化为乌有。这倒是没有发生,生命力是难以估量的,然而,发生的事可能比这还糟糕。 我小时候很胆小,当然,既然是孩子,我肯定还很倔,母亲肯定也很溺爱我,可我不认为自己特别难**,我不相信,一句和善的话、一次不动声色的引导、一个鼓励的眼神不能使我乖乖地顺从。你其实是个善良仁慈的人,但并非每个孩子都有坚韧的耐心和无畏的勇气,能一直寻觅,直至得到你的慈爱。你只按你自己的方式来塑造孩子,即通过力量、大叫大嚷和发脾气。 最初几年的事,只有一件我仍记忆犹新。一天夜里,我老是哭哭啼啼地要水,不是因为口渴,大概既是为了怄气,也是想解闷儿。你严厉警告了我没能奏效,于是,你一把将我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让我就穿着睡衣,面向关着的门,一个人在那儿。我无比惊骇,之后好几年,想象折磨着我。我总觉得,这个巨人,我的父亲,终极法庭,会无缘无故地走来,半夜三更将我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 你完全凭自己的本事干成了一番事业,因此,你无比相信自己的看法。你坐在躺椅里主宰世界。你的观点正确,任何别的观点都是荒谬、偏激、疯癫、不正常的。你如此自信,根本不必前后一致,总是有理。有时,你对某件事毫无看法,因此,对这件事的任何看法必定都是错误的。比如,你可以骂捷克人,接着骂德国人,接着骂犹太人,到头来,除你之外所有的人都被骂得体无完肤。在我眼里,你具有所有暴君都具备的神秘莫测,他们的正确靠的是他们本人的存在,而不是思索。 我俩不可能平心静气地交谈,这还有一个其实很自然的后果:我连话都不会说了。即使情形不是这样,我恐怕也不会成为大演说家,不过,像一般人那样流畅地说话还是可以的吧。你早早就禁止了我说话,警告我“不要顶嘴”,一边说一边举起手,这些都一直伴随着我成长。我终于哑口无言,开始时可能出于执拗,后来则是因为我在你面前既不会思考,也不会说话了。 你特别相信讽刺所产生的教育效果,讽刺也最适合表达你在我面前的优越感。你的警告通常是这样的:“你说不能那样做吗?这对你恐怕太难了?你当然没有时间?”诸如此类。每提一个这样的问题,你就狞笑一声。被问的人还不知道自己做了错事,就已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惩罚。 与你对孩子的这种态度极不协调的是,你经常当众诉苦。你怎么竟会期望得到同情?你在任何方面都是巨人,怎么会在乎我们的同情?后来我明白,你确实为儿女吃了很多苦,然而当时——在另外的情形下,诉苦可能会打动一颗坦率、无所顾虑、乐于助人的童心——在我眼里,这必定又不过是极其明显的教育和侮辱手段而已,手段本身并不很厉害,只是它的副作用很厉害,使得孩子习惯于把应当严肃看待的事偏偏不怎么当回事儿。 确实,你没有真正打过我。可是你的叫嚷,你的胀得通红的脸,你把背带放在椅背上随时待用,对我来说比真打我更可怕。我就像行将被绞死的人。若是真被绞死,一死也就没事了。如果不得不亲眼目睹被绞死的所有准备工作,一直到绳套已吊在面前了,才得知获赦,那可能会为此痛苦一生。 我要想逃离你,就得逃离这个家,甚至逃离母亲。虽然在她那儿总能找到庇护,但这庇护始终牵连着你。她太爱你了,对你太忠心,太顺从了,因而在孩子的斗争中难以持久地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这也是孩子的一种正确的直觉,因为随着年岁的增加,母亲更加依赖你了;当事情涉及她自己时,母亲总是温良而柔弱地维护着她那最低限度的独立,而且从不真正伤害你,随着年岁的增加,她却越来越——情感多于理智——全盘接受你对孩子们的看法和批评。 她因为你受了我们多少苦,因为我们受了别人多少苦,更不用说她因为纵容我们而受的苦。即便这“纵容”有时不过是对你的那一套的不动声色、无意识的**罢了。母亲若不是从对我们大家的爱以及由爱而生的幸福感中汲取了力量,怎承受得了這一切? 你一向是离店铺和家庭越远,就越和善、好说话、客气、体贴、富有同情心,就像一个暴君,一旦越出了他的国土,就没有理由老是那么暴戾,与再低下的人相处也和蔼可亲了。我则某种程度上一直蜷居于你的影响的最内在、最严厉的紧箍咒里。 你对我的写作及你所不知的与此相关的事所持的反感态度倒还有些道理。在写作中,我确实独立地离你远了一截,即便这有些让人想到虫子,它的后半截身子被一只脚踩着,它用前半截身子挣脱开,挣扎着爬向一边。我稍微舒坦些了,我舒了口气。这当然是一种错觉,我并不自由,境况最佳时也还是不自由。我的写作都围绕着你,我写作时不过是在哭诉我无法扑在你怀里哭诉的话。这是在拖长与你的诀别,只不过,这诀别虽是你逼出来的,却按我所确定的方向进行着。 而对婚姻的意义及可能性,我却几乎没有任何先见之明。我生活中的这件迄今为止最可怕的事突如其来地降临到了我头上。我成长得十分缓慢,这类事似乎离我远得很,偶尔才不得不想到它。而我始料未及的是,这里酝酿着一场持久的、决定性的甚至最严酷的考验。实际上,结婚的打算成了最壮观、最有希望的摆脱你的尝试。 正是这种与你的紧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使我渴望结婚。这样我俩就会平起平坐,我把这想象得十分美妙:结婚以后,我可能会变成一个自由、知恩图报、无辜、堂堂正正的儿子,你可能会变成一个不沉重、不暴戾、善解人意、心满意足的父亲。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一切往事都必须一笔勾销,也就是说,必须把我们自己抹掉。 两次结婚的想法都很正当:我想成家,想变得独立。这个想法你很赞同,但它在现实中破灭了,就像儿童游戏里,一个人一边抓着甚至紧按着另一个人的手,一边号喊道:“你走啊,走啊,你干吗不走?”而我俩的情形复杂就复杂在,你从来都是真心实意地说着“你走啊”,但你以你的性格从来都是阻止我。
这两个女孩的选择虽然出于偶然,却是精选细挑的。你竟以为像我这样谨小慎微、优柔寡断、疑虑重重的人会因为喜欢一件衬衣而心血来潮要结婚,这说明你又完全误解我了。这两个女孩没有让我失望,是我让她们失望了。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抚育儿女,甚至还加以引导,我坚信这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限。乍一看,许多人似乎轻而易举地做到了,但真正做到的人为数并不多。 (岐岐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变形记》附录《致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