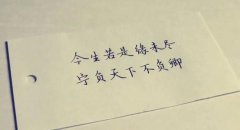母亲的顶针
|
母亲老了,卧床了。她的针线筐搁置在衣柜上,落满了尘土。里面的一些碎布头、缠线板、顶针等也仿佛固定在母亲卧床开始的那个年代。那枚顶针上有了斑斑锈迹,显示着主人许久未动了。那枚顶针虽然生锈,但它却是母亲使用多年的老件东西了。 说起顶针,有些年轻人就比较陌生了。因为它不像戒指那样受人青睐,它是用于缝补衣服的工具,上面布满了小坑,用来顶住缝衣针的后端用力顶,以便穿过厚厚的衣物,故名“顶针”。 这枚顶针不知道母亲使用了多少年了。这枚顶针是铜制的,很少生锈。因为一年四季母亲都带在身旁,不离左右。家里人多,需要缝缝补补的东西就多,因此母亲大多的时候都是带在手上的。母亲是个极细心的人,每当手指下水时,会小心的取下装在随身的内衣襟里。 在那艰苦的日子里,一家八口人的衣服、鞋袜、被褥都是母亲一人完成的,而使用顶针最多的地方就是做鞋和做被褥。做鞋时,母亲先用锥子把千层底使劲扎透,再借助顶针将钢针穿入针孔,很用力的。实在顶不动了,母亲会用牙咬或者钳子往外拔,为了结实,每穿一针,母亲都要用手把粗线绳拽住狠狠的勒紧,一双鞋底纳下来,母亲的手指都会勒出血来。做被褥相对轻松一些,因为被褥厚实,使用的针较长,更需要顶针了,不过力气不用太大。母亲左手在上压住被褥,戴着顶针的右手在下面顶住长长的缝衣针,很轻松的做完了一床又一床的被褥,使我们在漫长的冬天里没有挨过冷,受过冻。天长日久,母亲的手指骨节渐渐变的粗壮弯曲,套在手指中间的顶针就再也拿不下来,成了母亲唯一的“装饰”。 去省城读书的前一天晚上,深夜醒来,母亲仍在灯光下为我缝制衣服。灯光下,母亲一边擦泪,一边穿针引线,时而把针在她那花白的头发上一划,继续穿针。手指上的顶针在灯光下闪动,就像窗外天空的繁星。当时我的心里有些难过。后来每当读到诗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就会想起母亲的那个不眠之夜。 儿行千里母担忧,我走出了家门,却走不出母亲的心。每次洗母亲缝制的衣服时,看到那密密的针脚,就会想起母亲那佝偻的身躯,弯曲的手指以及那枚闪亮的顶针。 其实从一枚顶针的亮度,基本就可以判断出一个家庭主妇是否勤快,母亲的顶针永远是亮亮的。针的步履是艰难的,需要借助顶针来完成,就这样一针一线,一线一步,一步一环,环环相扣,一如生活的艰辛,一步一步循环往复的往前走。 一枚小小的顶针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一件衣服老大穿破了,缝缝补补老二接着穿,老二穿破了缝缝补补老三接着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们都是这样在母亲的缝缝补补中长大的。 顶针在母亲的手上,不离不弃,缝补了一辈子,直到母亲七十多岁不幸患了脑梗塞,才停下来休息,这一休息就是七、八年了。 母亲卧床了,那枚顶针一定还在等着母亲的使用。我接过母亲的针线筐,取出顶针,认真的擦拭锈迹,期盼着它再次回到母亲的手指上。 |